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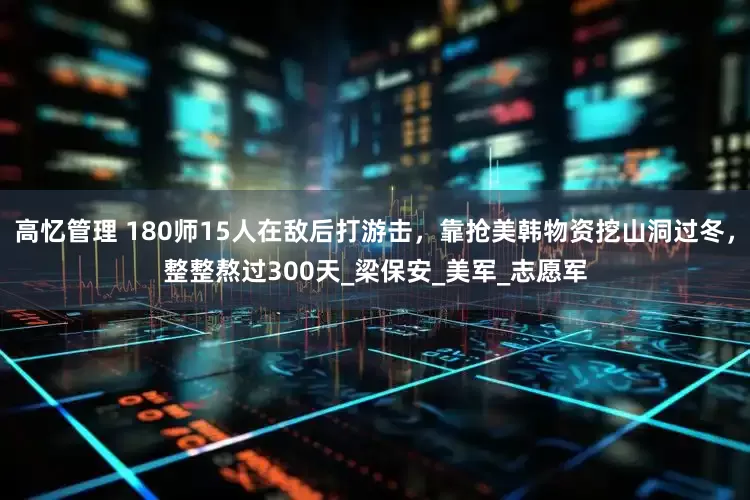
1951 年 5 月的朝鲜半岛,硝烟弥漫在北纬 38 度线附近的平原上。志愿军第 3 兵团 60 军 180 师的阵地前,美军的坦克履带碾过焦土,炮火如雨点般落下。师长郑其贵望着通讯兵手中的电报,眉头紧锁 —— 军部连续五次电令:"暂缓撤退,再阻敌 5 天,掩护全军伤员转移。" 此时,他们的弹药已不足三成,侧翼的 63 军早已撤离,180 师像一枚楔子,孤零零地钉在美军反扑的必经之路上。
断后的绝境:从阻击到被围
作为志愿军西线撤退的 "后卫",180 师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注定艰难。美军凭借机械化优势,在平原上日夜奔袭,而志愿军经过连续追击,早已粮弹两缺。郑其贵深知,每多守一分钟,主力和伤员就多一分安全。他下令各团梯次阻击,539 团、540 团、541 团像三道闸门,在美军的钢铁洪流前死死顶住。
阵地反复易手,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填补缺口。539 团二营五连在弹尽粮绝后,端起刺刀冲向美军坦克,最后全员阵亡;通讯兵在炮火中穿梭,用身体护住电台,确保最后的命令能传出去。直到 5 月 29 日,当最后一批伤员转移完毕,180 师才接到突围命令,但此时美军已从两翼包抄,形成了密不透风的包围圈。
军部派出 12 名通讯员和 181 师救援,却因联络中断错失时机。突围开始后,部队被分割成数股,有的战士壮烈牺牲,有的被俘后仍在抗争 ——539 团战士张文荣在战俘营假意投降,趁美军不备将手榴弹扔进运输机,与敌人同归于尽。而 539 团政治处的梁保安,带着两名战友钻进了深山,成了敌后游击战的火种。
展开剩余70%三人小组:在绝境中扎根
"我们不能死,更不能当俘虏!" 梁保安对身边的两名战士说。他们突围时只带了 3 支步枪、12 发子弹和一把刺刀,藏身于朝鲜中部的密林里。最初的日子,他们靠草根、野果和树皮充饥,白天躲在山洞里,夜晚才敢出来侦查。
一次,他们在溪边取水时偶遇另外两名突围的战士,五人组成了临时小队。梁保安知道,分散求生不如抱团作战。他定下规矩:不扰民、不恋战、专打落单敌军和运输队。他们借着夜色摸到美军哨所附近,趁哨兵换岗时夺走两支冲锋枪和一些罐头;在公路旁埋伏,用削尖的木棍扎破美军卡车轮胎,趁乱抢走车上的压缩饼干和弹药。
两个月后,小队扩充到 12 人。梁保安成了核心,他要求每个人都熟记地形,学会分辨可食用的野菜,甚至要会简单的朝鲜语。"我们不是打游击,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活下去,等主力打回来。" 他常对战友们说。
寒冬突围:用双手挖出来的生机
1951 年的朝鲜冬天来得格外早,11 月就已零下 20 度。深山里积雪没膝,战士们穿着单衣,冻得手指发僵。梁保安意识到,没有避寒之处,所有人都会冻死。他组织队员轮班挖掘山洞,用刺刀、工兵铲甚至双手刨土,两个月后挖出两个能容纳 12 人的山洞,内壁用松枝铺成 "床",洞口用树枝伪装,成了他们的 "冬营"。
为了过冬物资,他们冒险袭击了美军的一个小型补给站。梁保安带着两人化妆成朝鲜村民,摸清哨兵换岗规律,趁夜摸进去,扛回 20 袋面粉、10 件棉衣和几箱手榴弹。"够我们撑到开春了。" 看着堆在山洞里的物资,战士们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
寒冬里,他们互相取暖,分享仅有的口粮,有人冻伤了脚,就用雪搓;有人发烧,就嚼几把草药。梁保安每天组织学习,讲革命道理,唱《志愿军战歌》,山洞里的歌声,成了对抗绝望的火把。
最后的冲锋:12 人对 3000 美军
1952 年 3 月,冰雪消融,梁保安带着小队再次活跃起来。他们得知美军在附近有一支运输队,便在山谷设伏,成功炸毁 3 辆卡车,缴获了一批弹药和药品。但这次胜利也暴露了行踪 ——3000 名美军带着装甲车和直升机,将山谷团团围住。
"分散突围,到预定地点汇合!" 梁保安当机立断。激战中,他们遇到了另一支 15 人的志愿军游击队,两队合并后兵分三路。梁保安带着主力从美军火力最弱的西侧悬崖攀爬突围,战士杨明强为掩护队友,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军同归于尽;贾宝保在断后时被流弹击中,牺牲前还在喊 "快撤"。
最终,25 名战士中 18 人突出重围,与北上的志愿军大部队汇合。当梁保安向首长报告 "我们是 180 师的" 时,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—— 这支在敌后坚持了 400 多天的小队,用行动诠释了 "决不放弃" 的含义。
丰碑永存:不只是牺牲,还有坚守
180 师的经历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段悲壮的篇章,而梁保安和战友们的游击战,更展现了志愿军战士在绝境中的韧性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,却用最朴素的方式坚守着信念:活着,战斗到底,等主力回来。
如今,朝鲜的深山里或许还能找到当年的山洞遗迹,泥土中或许还藏着锈蚀的弹壳。这些痕迹无声地诉说着:战争的胜利,不仅属于冲锋陷阵的勇士,也属于那些在敌后默默坚守的灵魂。他们用生命告诉我们:所谓英雄,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刻,依然相信黎明会到来的人。
发布于:河北省通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